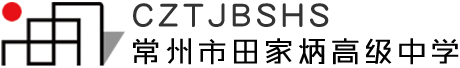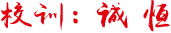作者:朱鲁子
摘要:“精神青春期”和“精神更年期”概念,是两个标志着人的精神生命发展的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概念,特别是“精神青春期”概念,它与人的创造力直接相关;“精神青春期”的阙如,意味着人的理性精神文明的创造力的匮乏。面对当下中国年轻人普遍缺乏创造性这一现实,彻底反思和改革我们的中小学(包括幼儿)教育和大学教育,把“精神青春期教育”纳入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关键词:“精神青春期”创造力“精神青春期教育”自律性现代人生哲学
研究团队:朱隽姿、曲经纬、吴文庆、邢燕燕、杜景凯等研究生
当下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青春期教育”,无非是关于“生理青春期”的教育罢了。这是一种好现象。然而,有一种较之“生理青春期教育”更重要的关于“精神青春期”的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青春期教育”,迄今尚未进入人们的视线。现代人生哲学[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提出的“精神青春期”和“精神更年期”概念,是两个标志着人的精神生命发展的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概念,特别是“精神青春期”概念,它与人的创造力直接相关;“精神青春期”的阙如,意味着人的理性精神文明的创造力的匮乏。因此,面对当下国人普遍缺乏创造力这一现实,在众所周知的生理性的“青春期教育”之外,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精神青春期教育”理念,就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教育理念认为,应该把“精神青春期教育”纳入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
一、“精神青春期”概念
“精神青春期”是一个标志着人拥有理性精神文化或文明创造力的概念。人类所有的理性精神文明成果,都是曾经进入过“精神青春期”的个体创造出来的。
现代人生哲学从逻辑上把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了自发性阶段、自觉性阶段和自然性阶段,认为人的精神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与个体生理发展依据生理青春期和生理更年期把人从生物性上划分的三个阶段即前青春期阶段、青春期-更年期阶段和后更年期阶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换言之,理论上说,在自发性阶段与自觉性阶段的转折点上,应该有一个“精神青春期”,在自觉性阶段与自然性阶段的转折点上,应该有一个“精神更年期”。这样,从精神上划分人生阶段,就有了三个类似于人的生物性发展阶段的精神发展阶段:自发性阶段(“前精神青春期”阶段)、自觉性阶段(“精神青春期-精神更年期”阶段)、自然性阶段(“后精神更年期”阶段)。简明如下:
生理三阶段:
青春期之前——童年
青春期与更年期之间——少年、青年、中年
更年期之后——老年
精神三阶段:
精神青春期之前——自发性形态
精神青春期与精神更年期之间——自觉性形态'
精神更年期之后——自然性形态[详见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第1-100页。]
当然,这种划分仅仅是理论上的。
就像没有生理青春期的个体缺乏生育能力一样,没有“精神青春期”的个体,缺乏的是精神生产能力——创造性——创造理性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自然赋予人的大同小异的生理青春期即生育、生殖能力,但,除极个别的天才人物之外,却很少有人拥有“精神青春期”即创造理性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我们的这种说法是从理论的严谨性和绝对性而言的,指的是“质”上的而非“量”上的。现实中并非如此。现实中,一般人或多或少地拥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创造力。]这是因为,前者是先天的不受人控制的,后者是后天的取决于个人的理性精神的觉醒和主观努力。现代人生哲学诞生之前,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关于“精神青春期”的概念,故在现实中,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应该拥有一个类似于生理青春期的“精神青春期”阶段,而缺乏对于“精神青春期”的教育和意识,就直接导致了现实实践中个体人生“精神青春期”现象的匮乏,并因此而缺乏创造力。——从现实中大众普遍缺乏精神文化或文明创造力可见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 w$ [. ^$ N7 @1 C
只有生理青春期的人生,充其量是在自然赋予的可能性空间之内完成了人生,这种人生无异于动物的人生;不仅有自然赋予的生理青春期,且有后天的“精神青春期”的人生,才能超越人的生物性层面而进入属人的精神层面
一旦个体进入了“精神青春期”,则将轻易地同化、吸收并掌握人类已有的理性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爆发出不可遏制的理性精神文明创造力,从而保障他在未来有足够的精神能量冲击下一个人生的关节点——“精神更年期”。这是因为,顺利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个体,其精神结构就完全转型为理性的“自觉性形态”,这种理性结构决定了,它拥有同化、吸收理性文明成果的功能,一如个体在自发性形态阶段里具有强烈的对感性事物的同化和吸收能力,如对语言和艺术的模仿能力。[此即结构与功能的同一关系。]这是一个人学习理性文明或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阶段。现实中某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等可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过“精神青春期”的个体,他们在向“精神更年期”迈进的过程中,为社会和人类做出“大贡献”和获得个人的人生幸福是不言而喻的。而那些未能真正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个体,是根本无缘“精神更年期”的。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人浪费了造物主的良苦用心。[在《轴心时代的阐释》一书中,我指出,轴心时代的先知圣人们现实地进入了“精神更年期”。光耀人类千古的轴心文明,就是这些进入了“精神更年期”后的特殊人类个体创造出来的。参见朱鲁子:《轴心时代的阐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4-166页。]当今社会令人棘手的所谓“青少年问题”,可以说,都与缺乏“精神青春期教育”从而使青少年缺失“精神青春期”有关。缺乏“精神青春期”,个体就很难同化、吸收并掌握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就很容易在人生之路上“走偏”,根本谈不上创造新的精神文明成果了。
二、个体生理发展规律与心理发展规律成反比关系
众所周知,进入生理青春期后,个体的生物性生产能力即生育能力到来了,这种能力一直会持续到个体“更年期”的到来而终止。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生育能力是呈由大至小逐渐衰退以至于彻底退出的趋势的。
与之相反,现代人生哲学(包括经验)告诉我们,个体在从“精神青春期”向“精神更年期”发展的过程中,其精神生产能力即创造理性科技文明或文化成果的能力是呈由小至大逐渐增强之趋势的。当然,人的既有的理性精神生产能力在“精神更年期”到来之后也是要“退出”的,但这种退出与生理更年期到来之后生育能力的彻底退出(丧失)不同,它是以自己发生质的转化或飞跃表现出来的:一旦个体跨过了“精神更年期”这道门槛,则其理性和的精神文明生产力将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能力——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生产能力——创造超越有限理性的直觉性的或“非理性”的精神文明成果(艺术性)的能力所取代。这时候,一种庄子意义上的超越有限理性的“大智慧”、“大智”将诞生。也就是说,“精神更年期”到来之后,虽然人的“理性文明”的创造能力退出了,但另一种更高级的精神创造能力诞生了。
由此可知,在那些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个体身上,其生物性生理发展规律与精神心理发展规律是成反比关系的:生育能力由强到弱以至于无,文化知识等精神文明成果创造能力由小至大以至于发生质的飞跃。[参见朱进富:现代人生哲学超星学术视频:《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20集),2012年5月,第一、第二集:http://{域名已经过期}/serie_400007905.shtml]不过,这种规律性在那些不能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个体——身心不能和谐发展的不正常的人——身上,却是失效的:现实中,芸芸众生一般来说身与心是同步退化的。
个体生物性生理发展规律与精神心理发展规律成反比关系这一规律的被发现和揭示,把人类迄今对于人自己的认识推向了一个科学的高度,其意义不可估量。可以想见,如果把这种规律性具体应用到基础性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甚至中老年教育上,必将使个体人生由于自我精神创造力的被发现或失而复得而发生空前的革命性的变化。正常人——身心和谐而全面发展的个体,必将在社会中大量涌现
此外,我们应该知道,因为与生理青春期到来相伴的,是个体对性快感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是无比快乐和幸福的,同样,“精神青春期”的到来,个体也将深刻地体验到一种非肉体的快感——一种由精神文明创造力所带来的神奇感、成就感、幸福感。而且,能够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个体,如无特殊原因,一般来说也将自然地进入“精神更年期”,拥有创造非理性的艺术性精神文明成果的能力。与这种崭新的伟大创造力相伴的,是个体对生命的最美好体验——马斯洛意义上的超越性的“高峰体验”。这种类似于(甚至高于)吸毒成瘾和性快感那样的极度幸福快乐的“高峰体验”,一般人是很难体验到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普通人一生中至多有一两次“高峰体验”。而这种体验在大艺术家和宗教家那儿是很普遍的。]这就与生理更年期到来后人的性快感彻底退出大大不同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诚如是:上帝在为他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一扇窗——通明瓦亮的天窗。只有在这样的人嘴里,才能发出人生是无限美好的感慨和感恩。对于他们而言,一年四季尽是好季节。
三、“精神青春期教育”是人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一个必要条件
“精神青春期”之于个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点也不差于甚至更重于生理青春期对于个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毫不夸张达说,“精神青春期”(包括“精神更年期”)概念的创造,对于人类及其个体来说,具有开天辟地的价值和意义。不过,这种无与伦比的意义,只有通过“精神青春期教育”方能实现出来:对于现代人来说,个体的“精神青春期”是“精神青春期教育”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那些自发地进入过“精神青春期”的个体,否则,就无法解释整个人类文明
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经验上说,人的精神的觉醒是晚于肉体的生理的觉醒的,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性意识的觉醒不可能在个体未进入生理青春期之前达到(人得先品尝性意义上的“禁果”的滋味后才懂得文明意义上的“智慧果”的味道,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现实中——现代社会,由于人类整体上迷失了本性,个体不仅没有“精神青春期”,就连自然赋予的生理青春期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变异。如,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知道的个体进入生理青春期的大致时间点是女子14(7的倍数)岁,男子16(8的倍数)岁,[“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耶,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写。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详见《黄帝内经》第一章关于“天癸”的理论。]而今,却早已面目全非了——每每见诸媒体的10岁左右怀孕堕胎少女的报道就是证明。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地区人种差异确认的个体进入生理青春期的年龄大致在10-20岁之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年龄规定为10一20岁,我国习惯上把12一18岁定为青春期,这是从儿童转变为成人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称为“少男少女”,比统称为“青少年”更为确切。在这个时期,性器官渐趋成熟,少女月经初潮,少男出现遗精,第二性征明显显现。参见朱坚、苗林:《青春期性教育需要全社会关注》,《中国性科学》2004年第12期。]我国有青春期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调查表明,我国青少年进入生理青春期的时间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每隔10-15年提前1岁。[2010年,中华儿科学会发布最新中国儿童成长发育专项调查结果:中国女孩的青春期发育开始年龄平均为9.2岁,比30年前提前了3.3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平均每隔10—15年,就提前1岁。”中国医学科学院博导、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丁宗一称,这个研究结论在1985年就报告过,只不过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参见2010年8月17日《南方日报》:《儿童“性早熟”为何成为常见病(图)》:http://{域名已经过期}/roll/201008/17/10000307_103293767.htm]这就是说,30多年来,我国青少年的生理青春期普遍提前了3岁,也就是普遍在11-13岁左右进入生理青春期。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一种生物的寿命是与其生理青春期成正比的。因此可以说,生理青春期的大大提前,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违反,更是我们人类个体的一个灾难。这种违反自然的现象从整体上颠覆了保持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素朴的身体生理发展规律。这就是发展、进步、现代化的“代价”。现代社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个体的自然生理规律发动攻击:物质层面的激素的滥用,精神层面的色情泛滥。——真不敢想象:某一天有媒体会爆出,某某幼儿园的小女孩怀孕了!- f3 R0 Z5 [' H
生理青春期的提早到来,会促使个体性意识的提前觉醒,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精神青春期”也会同时到来。
就像生理青春期的到来需要有一个性激素的增长积累过程一样,如果缺少了一个“精神激素”的增长积累过程,“精神青春期”也是不可能到来的。我们前面指出过,“精神青春期”一般不可能早于生理青春期的,而今,个体的生理青春期又大大地提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对个体来说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生理变化,会让小小年纪的少年人猝不及防,惊慌失措,疲于应付;特别是,生理青春期的到来所带来的生理上妙不可言的极大快感,往往容易把青少年引向道德意义上“堕落”的深渊——如“早恋”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淫欲。如此一来,青少年的精神注意力、精力就会大大分散和消耗,“精神激素”的增长和积累就难免泡汤了。可以说,生理青春期的过早到来,挤占、延迟、转移、耗费了“精神青春期”的发展空间;反过来说,如果青少年有一个正常的“精神青春期”,则会把他们从耽于感官的欲望如手淫、“早恋”等不良嗜好中解放、升华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何会有“万恶淫为首”的说法了(孔子有“少戒色”的说法:“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语出《论语•季氏》),也可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为什么会把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实为性经验意义上的“禁果”)称之为“原罪”了。[人们往往误以为基督教是在心理精神的意义上反对吃“智慧果”。这是非常荒唐的望文生义。]这是其一
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引发整个社会普遍不满的因素是当下的中小学(包括幼儿)教育。由于当下的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内容和方式的不科学,难以让个体增长和积累起足够导致“精神青春期”突破的“精神激素”,从而使得现实中的青少年不可能达到“精神青春期”的临界点,只能普遍成为“精神阳痿”患者。当然,当下的小学教育内容和方式的不科学,又是由我们当下以升学为目的的急功近利的教育目标——“应试教育”决定的。[这里必须指出,那些考上大学甚至重点大学的个体,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普遍地进入过“精神青春期”,事实上,他们与没有考上大学的个体之间的差别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须知道,幼儿和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融“冰”——融解自发性精神之“冰”,否则,就难以收获理性的自觉性精神之“水”;而这个过程,最最要紧的是要有“日凿一窍”(庄子《应帝王》)的耐心,循序渐进,而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在现代人生哲学中,我把自发性比喻为“冰”,自觉性比喻为“水”,自然性比喻为“汽”。参见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第38-44页。]给予少年儿童充分的系统性的“精神青春期教育”即自由的融“冰”式教育,把祖先遗传给人的自发性精神能量通过“快乐教育”的方式,如通过感性的游戏、艺术活动和模仿练习等等,使其尽量地表现、实现出来——转化为自觉性、理性能量,当是个体顺利地进入“精神青春期”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我们所谓的“精神青春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启蒙性教育,它类似于传统教育中的所谓“蒙学”教育。这种启蒙性的“精神青春期教育”,应该贯穿于个体“精神青春期”之前的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之中,比生理性的“青春期教育”重要得多。)
当下,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商人和不懂教育的教育者的鼓动诱惑下,唯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按照少年儿童的天性因材施教,恨不能“日凿七窍”,“一口吃成个胖子”,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导致“望子成龙的悖谬”。[参见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第65-66页。]个体大量的自发性精神之“冰”不能有效地融化,从而缺乏自觉性精神之“水”,这就从根本上阻碍(至少是延缓)了青少年进入“精神青春期”。而因此,本应在中学阶段对理性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少年人,却会表现出厌学情绪,相反,又会对网络游戏“成瘾”,对性“成瘾”。
四、亡羊补牢——补“精神青春期教育”课
对于社会中个体普遍缺失“精神青春期”这一悲哀的现实,我们现实中的每个成年人都需要作出深刻的反思,需要明确地意识到: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补“精神青春期教育”之课的可能性
首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成年人是否可以努力尝试重建自己的“精神青春期”,以为亡羊补牢?我想这是有可能的,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我们意识到了,那么,现实中的某些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需要的没有经济之忧的成年人,是完全有可能找回来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精神青春期”的,“大器晚成”不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的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父亲,27岁始发愤为学终有大成,与两个儿子并列文坛“三苏”的苏洵,不就是我们的榜样吗?年龄比较大的成年人如果能够自觉地通过系统的类似于“老年大学”之类的学习形式来补“精神青春期教育”课,或可发现自己身上拥有某种从未有过的领悟力和创造力,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受到生命的无限美好。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大量贪得无厌、庸庸碌碌的成年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同样有着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那样的潜能。另外,大量的青年人也属于成年人,他们中最优秀的都进入了各种各样的大学。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大学教育能否让他们失去的“精神青春期”失而复得,就至关重要了。非常遗憾,我们当下的大学教育也是急功近利的,若不从根本上予以改革,其是难以当此重任的。正因此,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和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但在科技文明和思想的创造方面,我们却是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鉴于此,彻底改革我们的大学教育,把给大学生们补“精神青春期教育”课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添加进去,可谓机不可失。
其次,为了我们成年人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重演,我们必须从“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悖谬逻辑中解放出来,尽最大努力,把“精神青春期”还给本该属于的青少年们。[这个课题太大了,它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非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
一方面,由于“精神青春期”的发展一般滞后于生理青春期,故,我们应该尽量延缓少年儿童生理青春期的到来。这样,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饮食方面考虑,尽可能地让孩子们远离激素类食品和药品,而且,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远离色情环境和色情产品,教育孩子们不要早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生理性的青春期教育方面,但真正科学的却非常少,人们注意到的多是表面现象。[2012年5月4日《新民晚报•新民网》:《现代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年龄提前小学生参与早恋》:“20年前,“早恋”发生在高中;10年前,“早恋”发生在初中;如今,“早恋”已经进入小学,并有上升趋势。”]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知道,孩子们早恋或热衷于生理快感,痴迷于“网络”,是与“精神青春期”的匮乏和无意识(未被意识到)有直接关系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匮乏补偿”或取代:青少年的精力没地方使啊!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应该努力让孩子们获得足够的保证其在生理青春期到来不久(当然最好是同步,但可能性几乎为零)就可以进入“精神青春期”的精神能量或“精神激素”。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革当下的中小学(甚至幼儿)教育体制,彻底抛弃急功近利的以升学为目的的幼儿和中小学教育,代之以使青少年拥有一个“精神青春期”为目的的“精神青春期教育”理念。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根本没有“精神青春期”这一概念,更缺乏科学的“精神青春期教育”,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来看极为匮乏。幸运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蒙学”教育思想比较丰富,或可借鉴。
“精神青春期教育”的关键时期是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应遵循的基本规律是启蒙式的“日凿一窍”即循序渐进,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使个体进入“精神青春期”。因此,找出青少年个体达成“精神青春期”的具体途径或方法,是我们正确地进行“精神青春期教育”的关键。我们研究的结论是,青少年个体进入“精神青春期”的唯一途径或方法,就是培养或养成他的自律性——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这种自律性的获得,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循序渐进的“习得”、“养成”的过程,它需要儿童从懂事开始就进行一个类似于宗教“斋戒”即严格要求自己一以贯之的实践过程方能达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各种宗教中所极力强调的“戒律”的意义了。]因为,非如此,青少年个体不可能积聚起足以引发其精神突变的精神能量。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少年人立志或树立理想的过程。而至于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内容,则与传统教育基本无异,无非是语言(特别是母语)文字和基础数学(算数),基本的天文地理历史生物知识等教育(其中,历史教育必须慎重),和相对专业的艺术门类教育(可由学生自由选择,我们强调技术上的专业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小学毕业之前(即个体进入生理青春期之前),必须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生理青春期教育”……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面对当下中国年轻人普遍缺乏创造性这一现实,彻底反思和改革我们的中小学(包括幼儿)教育和大学教育,把“精神青春期教育”纳入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意识即达到,理解即超越。”[参见朱鲁子:《轴心时代的阐释》,导论